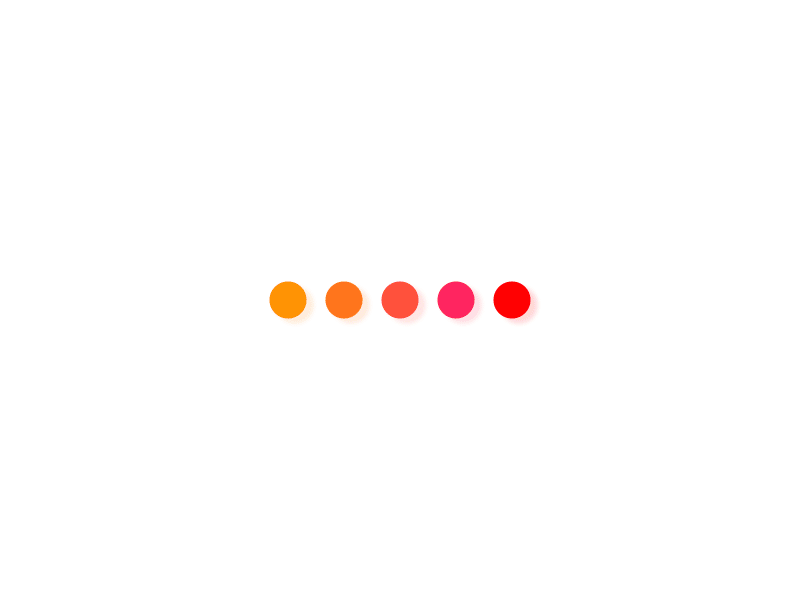“姓名?!”
“纪海成。”
赵雨乔瞥了瞥这个身材壮实、低头含胸的农村汉子,一边讯问,一边在笔录的性别一栏里填上个“男”字。
“年龄?!”
“四十八。”
“文化程度?!”
“初中。”
“身份――干啥的?!”
“农民。在外面打工,搞建筑。”
“家庭情况?!”
纪海成抬起戴手铐的褐红的双手,用粗糙的手背抿着汗津津的额头。满是尘土的头发和红铜色的面孔铸就的沧桑掩盖了他的实际年龄,仿佛生的长度已经超过了与死的距离。他张开粗硬如扒的手指,抓抓头发,没有回答赵雨乔的讯问,只是深深的叹一口气,把头埋进两膝中间。
“说说家里都有谁,每个人的详细情况!”
赵雨乔停了笔,瞟了瞟自己漂亮的字迹,然后直直地盯着这个蹲在墙角的人。猛一看,像是在审讯一堆洗得发白的蓝色旧棉布团。
同事纪振东进来了,手里端着个从饭店里拎回的盛草莓汁的小口大肚玻璃杯,绿茶还在热水里翻腾。由于烫手,他把杯子在两手间倒换两次后,放在桌沿上,甩着发烫的手指嚷,“说吧,咋不说话?有胆做,就没胆说?!”见这堆旧棉布团缩了缩,没有回话,走上前,扬巴掌朝纪海成的头顶扇了一下,“没种。瞧瞧,这是啥地方。你想说说,不想说就不说?!再不说,就该收拾你了。你以为干了啥好事,请你来哩。不说清,过不了关!要是吃稀饭不吃稠饭,等着挨哩?!”
纪振东两手叉腰,弯背伸头,拧紧了脖子威吓着。
躺在赵雨乔床上的司机栗有光一骨碌爬起来,湊上前,“还不赶紧说。娘个蛋,还饶了你?!”边说边踢了一脚。
“甭理他,让他说。”赵雨乔觉得他面相还算老实,也不想真的让人揍他,站起来,把椅子往后一蹬,怒斥道,“说!你媳妇叫啥,干啥的?!”
墙角的旧布团踡了踡,咽了一口唾沬。
“叫苏美英。”
“哪三个字?”
“就是苏联的苏,美国的美,英国的英。”
“名儿倒不小。干啥的?”纪振东拍了一下桌子。“说吧,还得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哩!”
“老百姓,种地的。”
“说农民就行了!”纪振东端起杯,吹吹茶叶,吸溜一口,嘲笑似的嚷了一句。栗有光哈哈了一声,接嘴说,“有苏联,有美国,有英国,就没中国。干脆,改个名儿,啊,叫――叫――叫‘联合国’算啦。哈哈――”
“说说子女的情况?”赵雨乔坐下了。他的话也像铁石一样硬,但少了许多刺和棱。
“闺女叫纪军平,出嫁了。孩子叫纪军强,十七了,跟着我在外当小工。快要收五月了,我俩才回来。”
“毕业后都干过啥?”赵雨乔怕他不懂简历的意思,就直接问。
“年青时当过兵,后来种地。这几年在外地打工。”
“以前受过打击或处理没有?比如判刑、劳教。”
“没有。”纪海成用袖子擦拭着脸上淌下的汗水,目光偷偷向上一晃,又赶紧收起,盯着脚上起毛的布鞋底子,那是女人一针一线纳的,这种布鞋现在在农村也不多见了。
“和纪海根啥关系?”
“兄弟俩。”纪海成又把头低了低,喉咙像是被捏住了。“他是我兄弟。”
“亲兄弟都动刀动枪,瞧你这人利害哩!是红胡子吧。”
“要是与其它人生气,你还不攮死他?!瞧你也老实巴交的,下手可不老实。”
“这倒好。住个三年五年,没人敢惹你了。横着走也中,顺着走也中,背着脚走,还中!”
纪振东和栗有光逼视着墙角的破旧布团,夹七夹八地敲打着他,像狮子按住猎物,仰天长啸,宣扬着胜利和威猛。
“不是我攮的。”他哀告般,怕挨打似的抬抬头,可怜的目光警戒着,膝盖牢牢的顶住胸膛。
“放屁!你兄弟自己攮的?他活腻啦,自己把肚子攮个窟窿,”栗有光又装模作样的踢了一脚。“嫌出气不匀哩?!”
“冤枉,冤枉!――”办公室里的怒斥声尚未落地,外面突然暴发了一声有力的嘶喊,像被叼走了崽的母狼般凄厉,响彻了派出所每个角落。
“娘啊,儿啊,老天爷哎!”
“谁?!”纪振东和栗有光反射似的一跳,大步出去了。
楼上楼下办公室里的人都跑出来,惊异地望着院子里又哭又叫的一老一壮一少三个妇女。年轻的少妇搀着老婆婆,只管抹眼泪。
纪海成一听哭喊声,呼地站起来,扭头向窗外看。赵雨乔把椅子一踢,急上前一步。纪振东的杯子被带倒,叭的打碎在地,滚烫的水把茶叶淌成一大片。赵雨乔一手抓手铐,一手揪肩膀,眼冒凶光:
“不许动!老实点。
“蹲下!蹲下!”
赵雨乔的双手感到了纪海成胳膊上肌肉的坚硬,但他没有反抗,而是顺从地蹲下了。只是不死心的伸长脖子,想透过门缝窥探。
“屈死人哩。老天爷,你睁睁眼哪。纪海根可是个老实蛋啊――。三岁小孩都知道,纪海成不是凶手――”她唱戏般悲悲切切,哭灵似的声音像铮铮的水袖,长而韧。
“没人性的纪海根,坑哥、害嫂,灭侄儿。你毁了俺全家啊:好人遭了殃,家破人又亡。千刀万剐的纪海根,皮儿不疼骨头疼。你讹干了雨,榨干了风,虼蚤没肉也剔半斤――。针鼻儿小,篦不住你的心;草鱼皮薄,你也要揭两层。葡萄藤的虫儿,桑树叶的茧儿,拱透了心儿,还不放过叶儿――你刻薄毒啊。小鸡吃石子,个儿小可肚里硬,活不久的纪海根啊……
“你毒过砒霜,狠过恶狼,冷冰冰一个青石阎罗王!――
“纪海成,你个死败种!不做活,光作孽――肥狗肉不上桌,薄驴皮下了锅。你耳扒扇不出个屁,驴蹄踢不出个声,――派出所冤枉人啦!俺的娘呀,屈死人哩。”
壮实的妇女见派出所的人都围过来了,便一屁股坐在地上,鼻涕肆意,手拍大腿,身子一仰三哈。像被兽夹夹了脚的熊,因为惊惧,顾不得疼痛而拼命长嚎。她身后的老太太佝偻着,喊叫着儿啊孙儿的。年轻的少妇一手挽着老太太,另一只手想去拉一把坐在地上的壮妇。地上的壮妇猛地甩开她的手,疯了般,朝自己的脸叭叭的打起耳光来。
大家明白过来这三个是纪海成的老娘、妻子和女儿时,便七手八脚地又拉又拽,想把祖孙三个劝到一楼户政室大厅。老太太见有人来拉,也不管个个口喊大娘,竟然“呸,呸,呸!”朝拉她的制服们吐唾沫,还翘起被日月和手掌磨得乌黑光溜的桃木棍手杖,要敲民警的头。年轻的少妇云鬓早乱,面露惊惶,慌忙按住奶奶的手杖,以免真的敲在大盖帽的头上。
壮妇等人靠近,一滚挺起来,鼻涕、唾沫喷了老远。民警们还未贴上,壮妇的两手已在他们的胸前领后揪了几把。她坚硬厚长的指甲,在粗大有力的十指的驱动下,像是一把把利刃,扫过对手的左肋右肩。只到壮妇的手脚被按住,大家要搬起来将她抬走。壮妇像受惊的母牛,连踢带蹬,又顶又撞。屁股一离地,她浑身扭动,张口就咬。民警王启吉哎哟一声,手一松,她扑通落地,如蛟入水。
披头散发的她已经认不出是男是女,像是一个古代的行者,嘶哑的声音从喉管深处涌出后变成低吼。
一群男子败下阵来。拍腿的拍腿,正领子的正领子,揉眼的揉眼,跺脚的跺脚,面对眼前这个摸爬滚打的壮妇,竟一时失去了战斗力。崔巍摩挲着头发,支楞着头顶,气愤的骂着。他不是惋惜发型的破坏,一缕头发还在壮妇手中死死的攥着哪。
“恁利害呀!”赵一君跺跺脚,不紧不慢的说。
“二熊!还咬人哩!”王启吉跳出圈外,憋紫了脸。
大街上的闲人闻声而聚。壮妇见民警失势,看客也多了,都给了她巨大的鼓舞。她再次披发摇头嘶喊,暴怒的、长角般朝拖抬她的民警猛扑猛撞。她不管衬衣上不同颜色的扣子迸掉了几颗,衣襟翻卷在胸口,贴身的、带洞的小褂子裂开,蹬踢的裤管扯在膝处,露出白白胖胖的肚皮、腿肚子和一只没穿袜子的大脚,像翅膀受伤的鹰胡乱扑闪。见抓不住躲闪的民警,就顺手捞起旗台边一盆怒放的紫月季,举过头顶,反躬腰身,狠狠的摔向眼前的死敌。围观的人群哗地撕开个口子,等花盆和土在地上刺耳的惊叹过后,再哗地合上。她又捡起烂成一团的月季,奋力向人群扔去,骂一句,“我日你娘!”人群哄笑着躲开了。她见屡屡落空,就四仰八叉躺在地上,失控的马达般,白白的肉团在地上翻滚起来。
“母老虎!大男人也降不了哩。”栗有光不要脸的说笑着。
“打人哩,打人哩!公安局打人哩!――”她喊着。
喊叫声吸引来的人越聚越多。从空中鸟瞰,人们围成个移动颤抖的巨型花环:紫红衣服的农妇像是花心,草绿色衣服的民警像是花瓣,围观的人群像是花萼,蚂蚁寻食一样往派出所里赶的人组成花枝。
“派出所凭啥抓人?!纪海成一没杀人,二没放火,犯了啥王法!你都这些东西,人皮包着狗骨头!――羊粪弥了眼,鸡屎蒙了心!阎王爷饶不了你都,阴曹地府等着哩――滚油的锅儿,烧红的链儿,又尖又利的小铁叉儿。来吧,打老娘吧,老娘不活了。老娘活不成啦。派出所的打人哩,公安局的打人哩。派出所打死人哩,公安局打死人哩!――”
看热闹的把派出所围个水泄不通,像是受难的人群挤在一处,翘首以盼一架满载救援物品的嗡嗡响的大型直升飞机。
“出啥事了,出啥事了!”
“唱戏哩!穆桂英大战天门阵!”
“别挤!瞧你,踩着我的脚啦!”
“呃,后面的人往前涌呐!”
“甭挤,前面也看不见呐!”
“别吵啦。瞧!母老虎吃人哩。”
“这娘们,长对獠牙就好啦!鲁智深、李逵也不敌!”
“站着尿的鲁智深、李逵死绝啦!”
“这年头,啥事都有!闹吧,不闹没人管。”
“人太少,再闹也是一个人啊。十个八个才有声势!”
“一泡稀屎拉脚面上,派出所也没拿了!”
围观的人们像非洲草原上的一群秃鹫,你一口,我一口的叼着横在草地上的支离破碎的、叫人恶心的腐尸。
“启吉,要帮忙吗,在你、都、这、儿、闹,太不像话了!拿手枪,崩了她!”镇上的几个熟面孔幸灾乐祸的高叫着。
“巴不得起哄哩。”民警王启吉扫了对方一眼,嘴里咕噜一句。乡办民警张日升嗔骂到,“就你嘴长,磁县夜壶,不装啥好水!甭瞧啦。出去,都出去!”
人群撵过来,转过去。
“君子动口不动手,都暗地里给派出所使劲儿哩。”
“夜里回家使劲吧!光了屁股再使劲吧!”搭着他肩的伙计拍拍他的肩,取笑到。
“去呀,把宣传画往她身上一贴,她保证懂法懂理。一开窍,就不闹了。说不定,还鞠躬哩!没准儿,明儿送面锦旗!”
“瞎扯!派出所的是崂山道士啊?!”
“打110。‘110、110,一要就灵!’”
“轻点吧,老兄。瞧你,喷我一脸唾沫!”
“拉警报!拉警报!”一个半大小子扬着脖子,一跳一跳的喊。
“别乱,小子!”
“让开,让开!”一个想变成钉子的男子踢着苏美英挣脱的布鞋,一边往中间挤,一边吓唬小孩儿似的喊。“砸住头啦,砸住头啦!”
二、三十分钟后,派出所所长高海川和二瘦一胖三个人推开人群进入户政室,砰地把门关上。被连拉带劝到户政室里的老太太,用手杖往花岗岩地板上一捣一捣的,见到来人后,呸了一声:
“你都管不了!
“不见俺家小蛋,我就不走。人是我扎的――捉了我吧。”她一伸长满老年斑的左腕,往所长身上靠,“来,捉我吧,我去住监。老骨头,没出息,就当柴禾烧了,不要啦!”咚咚――拐杖捣着地板。
“大娘,谁把小蛋捉走了?!海成、海根两大人的事――不干咱小蛋的事。小蛋不是――跑了――不在家?没人捉小蛋。咋会捉小蛋哩。”村支书纪春明一指。“这是所长,不信,你问问。”
“是啊,是啊,没捉小蛋。大娘,没抓小蛋。”高所长赶紧肯定了支书纪春明的说法。
“不听,不听!狗念经,蛤蟆老鼠都不听。我没糊涂,甭诓我。诓人下阿鼻地狱哩!”老太太一字一字地咬着,十分坚定。
“没诓,没诓。我和春明都叫你大娘哩,你恁大岁数了,俺都咋会诓你。不会诓你。”村主任纪增山帮腔。
“你叫你本家侄儿广庆说说,小蛋早跑了,就不在家,派出所咋会捉他。”支书一边捉住老太太的左肘往椅子上按,一边说。
“甭急,大娘,先坐下。你老了,先坐下。没捉你孙子。”所长伸手去扶老太太拄手杖的右手。
老太太猛地把右手往怀里一拐,甩脱所长的手,气哼哼的嚷到:
“装好心,扯断人的脊梁筋。我还不该死哩。稀罕你拉我!”
“大娘,你消消火。都没诓你!大娘,你问问军平。”村治安主任纪广庆连忙拉拉军平的胳膊,想让她来证实他们的话是可信的。“军平,你给奶奶说说。”
纪军平没有做声,只是低了头抹泪。
支书纪春明看了看,对老太太说:“大娘呀,你瞧着俺都光屁股长大的,都不会诓你。要是有人诓你,就只有你家‘帝国’诓了你,派出所没捉小蛋!你老了,可一不糊涂二不迷,你想想,‘帝国’的话能听――她嘴片儿刮风,舌头尖儿下雨,耳朵孔都会放屁――多能瞎说。”支书又扭过来,“军平啊,你得给奶奶说实话哩,你奶奶恁大岁数了,要是有个闪失,可没法整。你当孙女得负责哩!”
老太太见孙女不吭气,跺跺脚,抢白到,“嫌奶奶死得慢哩,咋不给我说实话!”
纪军平仍不说话。村长纪增山埋怨到,“瞧你这闺女,给你奶奶一句安心话不就完了!在这儿越闹越丑,越闹越大――这儿是哪儿,是派出所!赶紧给你奶奶说说,是不是没捉小蛋?!”
纪军平没了退路,泪眼哗哗地,哇的哭了一声,哽咽着说,“奶奶,军强没叫捉来。”
“咋诓我哩。平儿,你也诓我哩?!”老太太又往地上狠狠地捣了捣手杖,歪头质问哭泣的孙女。
支书纪春明见状,急忙对治保主任纪广庆说,“快些儿,叫个车,先把大娘送回家。恁热的天,有个山高水低的,咋整。”
老太太干净利索地提提手杖,撇撇没牙的嘴咕哝,“走,闺女,咱走哩。小蛋没事就中。你爹你娘,咱不管。他俩想上天,想入地,当神作佛咱不管!”
看热闹的人群被赶到了外面,几个还不死心小青年的扒住门垛,探头探脑的往里张望。
送走了老太太,所长高海川让支书纪春明和主任纪增山去劝劝苏美英。纪春明一摆手,说,“甭急。先到你办公室,先到你办公室。”纪增山干脆一瞪眼,“甭搭理这糊涂蛋!”
纪春明吐出一口烟,弹弹烟灰,往沙发上一躺,不紧不慢的揭开了苏美英的老底:苏美英是二婚,从史家寨改嫁到东营村十来年了,人肯出力,就是脾气暴躁,张嘴不说话,拉硬驴粪蛋哩――一字一字都砸人。自她嫁到东营,方八邻近就没有一天安生过:一三五和妯娌吵架,二四六和邻居生气。晴天咒太阳,雨天打孩子,不晴不雨骂朝庭。反正没一天闲着。擀面杖天天举在手上,从来不是用来擀面条的。家里的粗活都要她做主,穿针引线倒是个门外汉:寨扣子,缭扣门,都是纪海成的差使。治保主任纪广庆是他三服里的本家兄弟,数说过她一回,被她点着后脑门,撵到家,骂成个龟孙儿。广庆这个管治安的副主任不敢和她打照面,远远的望见了就顺着墙根儿溜走。三街四坊、左邻右舍没有不和她吵过架的,就连同村的亲姑夫,她都拖着扫帚在大街追着打。因为名字叫苏美英,村民给她起个外号:“三大帝国”,还有的叫她“妇女主人”,是东营村钉嘴铁舌的货色。
赵雨乔记完笔录,把栗有光喊进办公室,叫他把纪海成看好,碰上门,自己到所长办公室听听情况。
“甭怕,叫她闹吧,闹够了再说。现在咱越劝,她越有劲儿。”支书纪春明从嘴里喷出一股浓烟,“实在不中,叫咱主任收拾她!”
“过一会儿,她要再不听说,我干她一顿:三拳两耳扒子,管叫她服服帖帖!”纪增山挺挺胸,哑着嗓子说,“再不了,弄折她一条腿!拖走她!”
所长宽大的老板桌上的电话响了,所长拖过话筒听了听,是刑警队的付浩昌与高松树要来所里查询一个人。
大家正在议论,外面又乱起来。“三大帝国”再次与民警们混战一场,要冲上二楼,被人拽住。她就抱死了赵一君的腿不撒手,脸上的涕泪汗垢拼命的抿在他的裤腿上。赵一君起钉子般一根一根扳松她的指头,其它人又拉又拽,撕胶布一样把她撕下来。她一骨碌半爬起来,身势如鹰,五指似爪,劈裆向赵一君抓来,“我揪掉你的……”大家又将她胡乱的按住,她的下半截话也没叫个清楚,身子仍在七八个气喘吁吁的男子们的手中又纵又挺,喷吐着粘痰,向所长办公室冲,要与在所长办公室的赵雨乔――抓她男人的男人决一雌雄。
“姓赵的,你下来,我咬死你。老娘今儿,肉磙子碾磨盘,碾不死你磨死你!” 她暴发力释放尽,声音变得低哑,但意志仍然坚挺,抓着一只布鞋,用鞋底子叭叭的打着地,继续念曲儿般哼哼着骂,“――黄皮狗,遥街走,翘高尾巴吐舌头。见人就呲牙,遇鬼紧低头。穿绸的当爹娘,#14815;篮的是对头。四处找屎吃,咬了小孩咬老叟。是人不当人,是狗终是狗!”
她骂完一阵,恶狠狠的蹬得栏杆铮铮的颤。她失望般停顿了一下,闭上眼,小孩子赌气般嚎了一嗓子,头朝下,锤子般朝木扶手咚咚的碰。
赵一君嘟噜个脸,嘴里不停的嘟囔,两手不知所措。
不知道纪海根怎么突然跑了出来,伸出戴手铐的手去拉自己的老婆。冷不防被苏美英一把揪住头发:来吧,攮你娘的眼儿,攮你老娘的肚!劈头盖脸的一通乱抓乱挠,一时将丈夫弄成了大花脸。
纪振东和栗有光又喊又叫,把纪海根抢出来,拖进办公室。
为了她的安全,大家再次涌上去,把她拖到院子中间宽敞处。七手八脚中,崔巍狠狠的踢了她两脚,大骂,太利害啦,不是人!
不知是她身体麻木了,还是没了力气,挨了踢骂,除了垂死般的啼叫,竟然没有多余的反应。
所长高海川站起来,往窗外望了望,抓抓粗壮的胳膊,嘿嘿了一声,“刑警队有两个人就来了。老纪,你去唱白脸。”他又扭头对村主任说,“增山,你去唱黑脸。”
支书纪春明从出来,大步走到她身边,俯身对她哎哎两声,趁“三大帝国”稍作安稳,湊到耳边,一脸神秘,偷偷地说,“嘿,不敢再闹了!不敢再闹了。再闹,出大事儿哩!”纪春明紧张的一回头,“所长给刑警队打电话哩――我听那意思,要连你一块儿处理哩。家里没了海成,还指望你主事哩。刑警队一来,咱可就当不住家了。你再犟,还犟得过公安局?!趁人家还没来,走,走,赶紧走!”
隐隐的警报声传来。
村主任站在所长办公室门口,八叉着两腿,粗着嗓子,远远的叫嚷,“死眉眼的东西,瞧不开眉高眼低。不撞南墙你心不死,不撞破头你不死心。监狱不缺你一个,瞧吧,一会儿――就一小会儿,瞧你咋整哩。闹吧,疯吧,全家都住监吧――还要那片脸不要啦。往后咋过时光哩,不在东营村丢死那人!”
话语未落,一辆213警车拉着警报,闪着警灯,卷着风尘,冲进派出所,嘎地一声刹停在花坛的正前方。车上跳下两个又高又壮的民警。瘦高的付浩昌戴着一副大默镜,活像一个美国大兵。他“咣”的一声把车门摔上,一抬下巴,厉声叫到,谁闹事哩!闹事的在哪儿!闹事的在哪儿!弄到公安局,拖进地下室,治治,服了劲,再塞进南监!了得哩,共产党治不了谁!!我倒要瞧瞧,谁比公安局还厉害哩!他打开枪套,把枪栓拉得哗啦响。高松树在后面夹着一个黑色的皮包,右手拎着一副手铐,一边抖一边喊,刑警队光治这地痞流氓不说理的主儿。市区扫尽了,横河又冒出尾巴啦。今儿,就来和她试试。不信,老鼠日猫。大白天,小鬼吃了阎王爷啦!
“人哩!人哩!”两人跺得楼梯咚咚响,旁若无人地从楼梯旁大摇大摆的迈过。走到所长门口时,付浩昌撩起帘子,脸朝外装腔作势的喊:
“关了大门。不能放走一个!”
支书纪春明前面拖着“三大帝国”的手臂,纪增山五指作叉,在后面伸长胳膊叉住她的后颈,“三大帝国”闭眼哼哼,身子不情愿的往后躺着――三人像是在播种,耕耘着派出所这片坚硬的土地。苏美英右手扯着撕成布条的上衣,不停的往裤带里掖,想裹住受了杂乱目光羞臊过的肚皮。
大门外的人如羊群紧随头羊而去。派出所一下子安静了。
次日早八点,所长高海川把提包刚放在桌上,小红旗旁的电话就响了,是东营村支书纪春明打来的。他说昨天回村后,“三大帝国”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在大街摔个稀巴烂,在大街当了一夜的“妇女主人”,跳着脚,指天骂地的把村干部当汉奸、走狗、伪保长、垃圾骂个遍。要不是拦着,村长纪增山早就抡拳上去了。又说,事情也算了了,总算摘了一顶愁帽。
“嘿嘿,嘿嘿。”
声明:本文内容整理自网络,观点仅代表原作者本人,投稿号仅提供信息发布服务。如有侵权,请联系管理员。